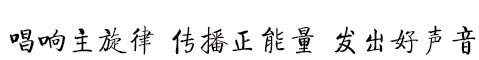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蔡传兵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聂耳诞辰110周年,从2月起,玉溪市举办了一系列以“聂耳和国歌”为主题的文化活动,纪念这位划时代的音乐家。时代洪流滚滚向前,聂耳,永远是朝气蓬勃的玉溪青年,永远是风华正茂的音乐家。聂耳用音乐作品为千百万被压迫者发出奋起反抗的吼声,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今天听来仍然具有惊雷般震荡人心的力量。回顾聂耳匆匆却又永恒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的名字与他的作品载入国家史册,成为不朽,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家庭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一个传统的玉溪中医家庭。
聂家的祖宅位于新兴州城内鲁贤祠街,今称北门街。父亲聂鸿仪是玉溪的名医,素有“着手成春”的美誉,却难以维持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大约在1902年,聂鸿仪带着家人到省城昆明谋求出路,先在端仕街租房开设“成春堂”医馆悬壶济世。两年后,他将玉溪的20余亩田地典让给一位商号老板,筹到纹银600两,将成春堂迁到甬道街七十二号的出租房内。这里距云贵总督驻地制台衙门不远,属闹市区,到成春堂看病的人也就多了起来,一家人的生计才有了转机。
聂耳降生时,以蔡锷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成立云南军政府。聂家租住的甬道街七十二号原属制台衙门公产,后归军政府所有。军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这类公产的房租翻了一倍。聂鸿仪无力承担上涨的房租,无奈带着家人在昆明城中迁移不定。不停地搬家,严重影响了成春堂的经营,聂鸿仪只得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做兼职军医,以微薄的外快补贴家用。
聂鸿仪在昆明行医十余年,为一家人的生计操劳十余年,还是没能让妻儿过上富足的生活。1916年,聂鸿仪患上肺结核病,为治病耗尽家中钱财,也没能阻止疾病夺走他正值壮年的生命。
聂耳的母亲彭寂宽,峨山县人,祖上属新平县漠沙镇的傣族傣雅支系,俗称“花腰傣”。她为聂家生下三男一女,在丈夫离世后接手成春堂的业务,自学医术,以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辛为4个孩子撑起了一个贫苦却又温馨的家庭。
聂鸿仪死后,彭寂宽带着孩子仍然无法摆脱迁移不定的生活,一家人先搬到了威远街菜市,不久又从菜市搬到端仕街,没住几年又迁到了更为僻静的青云街……年幼的聂耳接触到了挣扎在城市最底层各行各业的贫穷百姓,也尝遍了人世间的冷暖疾苦。
彭寂宽勤劳、热心、开朗,这一点与玉溪的傣族乃至许多少数民族女性非常相像。除此之外,她的身上还有很多优点:第一是节俭。第二是善良。她非常同情与她一样贫苦的劳动人民,尽管家里不宽裕,还是经常救济行乞的穷人,免费为许多穷人看病,并免费配药。第三是乐观。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表露悲哀,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想给儿女带来麻烦。她的这些宝贵的精神品质,深深地影响了聂耳,以至于《卖报歌》《码头工人》《苦力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歌曲都融入了聂耳关心底层劳苦大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体验。
成长
彭寂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尽管生活清贫,但她还是想方设法让3个儿子上学,同时言传身教,教子女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她常对子女们说:“这个家,这个窝,虽然说没有金子、银子,但是要有骨气、志气。”
彭寂宽成了聂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5岁时,聂耳就跟随母亲认识了几百个汉字。1918年,由亲友垫付学费,聂耳进入昆明县立师范附属小学。他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勤奋苦读,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聂耳识字后,彭寂宽经常用“唱书”的方式给他说唱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故事。唱书是当时玉溪民间劝人为善的一种曲艺,形式自由,有说有唱,唱词可以是“随口调”,也可以唱花灯调、扬琴调、民间小曲、山歌,甚至滇戏腔调。
往往一天辛勤劳作之后,彭寂宽就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给他们讲唱书中的故事,如《安安送米》《孟姜女哭长城》《柳荫记》……讲到动情处,母亲就会用玉溪花灯的走板调、全十字、扬琴调等对照着唱本上的韵文吟唱起来。幼年的聂耳常常依偎在母亲怀里,聚精会神地听着。故事中感人的情节,配上母亲深情的声调,常常让聂耳感动得流下眼泪。后来,聂耳在向友人谈起自己的音乐修养时说:“至于音乐,虽然一直很喜欢,但是在这方面的训练很少,有限的一点儿音乐修养,不过是儿时母亲吟唱的玉溪一带的民谣……”长大后,聂耳天生的乐感、独特的灵气,正是受了母亲的耳濡目染。
1922年,聂耳转入求实小学高级部之后,对云南丰富优美的民歌、花灯、滇剧、洞经更加热爱了。为此,他向邻居邱木匠学习吹笛子,后来又学会了二胡、三弦、月琴、风琴等乐器。学校成立儿童乐团,聂耳成了乐团的组织者和指挥。
1925年,聂耳考入学费低廉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这一时期,他开始阅读《东方杂志·列宁专号》、《环球旬刊》《生活知识》《创造月刊》,以及鲁迅的著作等进步书刊;投入蓬勃的学生运动,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组织的募捐、宣传抵制日货等活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喜爱当时群众中流行的《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中外革命歌曲;常在学校或家里与亲友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和番》等民间乐曲。晚上,他坚持到柏希文(曾任蔡锷的政治顾问)主办的“英语学会”补习英语,两人熟识后,聂耳还向他请教音乐理论常识和钢琴弹奏初级知识。
中学时期,每逢寒暑假,玉溪老家便成了聂耳的天堂。儿时的伙伴经常带聂耳去护城河里游泳,去郊外爬山,去寺庙里听洞经,去庙会上看花灯、滇剧……他们是真正把欢乐带给聂耳童年的人。聂耳还经常抽空去拜访陈茂先和鲁士贵等民间艺人,向他们学习玉溪的民间音乐。
陈茂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琴师,能演奏二胡、琵琶、古筝等乐器,且身怀反弹琵琶的绝技,对花灯、洞经、滇剧烂熟于心。他常在聂耳的邻居冯子钧家玩乐器,聂耳多次得到他的指导。
1927年,聂耳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师”)高级部外国语组学习英语。这所学校食宿都是公费的,但是保证金和书籍、被褥等物品的费用必须自己出。聂耳说服了母亲,向亲友借来钱才得以入学。这一时期,聂耳结识了新邻居、省师附小音乐教员张庾侯,并在他的帮助下开始练习小提琴。在学校里,他参加了共青团领导的外围组织“读书会”,1927年底开始阅读马克思的文章。1929年,聂耳在日记中抄录了马克思的简历,及其关于阶级斗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等论述。课余,聂耳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在一起演奏《伏尔加船夫曲》《梦幻曲》等名曲。
1930年7月,聂耳从省师毕业,家中已经无力让他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希望他早日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毕业前,玉溪县教育局局长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回到家乡出任县督学或到县立中学任教,他当面应允下来。想不到的是,他刚从省师毕业就被叛徒出卖,上了反动派的黑名单,匆匆踏上逃亡之路。
可即便身处异乡,聂耳也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对音乐的热爱。由于他早早地就确立了“为社会而生”的远大理想,社会便成了他最好的大学。
觉醒
聂耳革命意识开始觉醒,可以追溯到他在省师读书时期。
这一时期,正是昆明学生爱国运动高涨的时期,省师是当时昆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左右两派的斗争十分尖锐。聂耳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经常参加游行示威和文艺宣传活动,思想十分活跃。在昆明,他参加了旅省的玉溪同学组建的“玉溪青年学术研究会”,组织者是中共地下党员、共青团员,工作目标是宣传新科学、新思想,唤醒广大民众。从1927年至1930年,聂耳利用寒暑假先后4次和同学一起回到家乡玉溪,除了探访亲朋好友、向民间艺人学艺外,主要就是组织开展进步文艺宣传演出。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云南很快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时有革命者被捕牺牲。1928年3月,聂耳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女党员赵琼仙宁死不屈、英勇就义的壮烈场景。
聂耳作为党领导下的“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成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曾数次去监狱探望、接济被关押的革命同志。
这一时期,聂耳曾在作文《我的人生观》中疾呼:“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因而,应当“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在敌人的血腥屠刀面前,聂耳没有被吓倒。1928年8月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李国柱同志约见聂耳,地点在翠湖边上,他们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不久,入团申请书就批下来了,聂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9年7月11日,昆明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七一一”火药库爆炸事件。爆炸发生在城内的居民区,致使近千人遇难、上万人受伤,受损房屋不计其数,数以万计的居民无家可归。
此时,中共地下党成立了“七一一”青年救济团参与救灾,救济团的主要成员便是省师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李国柱、聂耳、马克昌(通海人)、刘希禹等人都参加了救灾。他们为灾民发放救灾物品、烧水、做饭、募捐棺木安葬死者,还捐出家里的财物购买药品医治灾民。在救灾的同时,聂耳、马克昌等人向群众宣传揭露了大爆炸的真相:军阀混战带来了这场大灾难。之后,他们又组织灾民与地方当局斗争。
为此,恼羞成怒的反动当局大肆抓捕革命志士,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聂耳等人因参加革命活动被秘密监视。
1930年7月10日,18岁的聂耳因叛徒出卖被迫离开云南来到上海,第一份工作是在云南人开办的云丰申庄负责采买香烟,并发往昆明,每月15元的薪水。此时的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了彻底破坏,很多共产党员被抓、被杀,一片白色恐怖。但是,每逢南昌起义、十月革命等无产阶级的纪念日,聂耳总是满怀激情地跑上街头,加入革命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11月,经同乡郑易里介绍,聂耳参加了党领导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之后又加入“苏联之友社”“左翼剧联音乐小组”等革命组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聂耳开始读《反杜林论》,同年9月正式考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后恢复为明月歌剧社),任第一小提琴手,月薪25元。
1932年4月,聂耳通过田汉与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直接联系。与田汉会面时,他倾诉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憎恨,对共产党组织的寻求与向往,决心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党,以音乐为武器为革命做更多的事。之后,聂耳开始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活动,以“黑天使”为笔名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对明月歌剧社老板黎锦晖追求“为歌舞而歌舞”的主张及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靡靡之音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引起黎锦晖不满,他便毅然离开明月歌剧社。
1932年8月,聂耳抵达北平,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失利后进入北平左翼剧联工作。10月28日,他随剧联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义勇军募捐的游艺会,并登台表演,用小提琴独奏了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11月,因长期找不到工作,聂耳只得返回上海,仍在上海左翼剧联工作。
1933年初,经过革命斗争的锤炼与党组织的培养,聂耳的阶级觉悟与政治水平不断提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求索
在上海,聂耳与党领导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直接联系后正式开始音乐创作,他在创作、思想上迅速成长,并走向成熟,显然跟我们党对他的培养、锻炼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入党之后,他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发挥。他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是在此后一两年内完成的。
进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后,他多次去听上海专业乐队演奏的贝多芬、瓦格纳、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又去听专业国乐队演奏的广东音乐。通过参加演出,听音乐会、唱片,研究各地的民歌、戏曲、古琴谱、昆曲谱、雅乐谱,聂耳学习、欣赏了大量中外音乐名作,扩大了艺术视野,丰富了音乐修养。之后,他学习和声、对位、作曲法等音乐理论,以及汉语发音、声韵变化、词曲结合等语音知识,并开始练习作曲。
由于缺少老师指导,聂耳在西洋乐器演奏上走了不少弯路。为此,在工作稍稍稳定后,他就从少得可怜的薪水里扣出学费去学习小提琴,先跟意大利籍私人教师普杜仕卡学习,每周一次要3元钱。出走北平寻求出路的那段时间,他也抽出时间去找俄国籍私人教师托诺夫学琴。1931年底,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海菲兹在上海举办独奏音乐会,聂耳向朋友借钱买票去听大师的演奏,受益匪浅。
故乡玉溪的花灯、洞经、滇剧,是聂耳记忆口袋里的珍宝。到上海后,聂耳曾多次写信给云南的亲友,要他们帮忙搜集云南的民间艺术资料寄给他。1933年,他写信给母亲,信的末尾有这样一段:“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将(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剧牌子都要。千万急!”
很快,尚处于失业状态的聂耳却在1934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宣称:“一九三四年是我的音乐年。”这是一句预言,也反映了聂耳走上革命音乐之路的自信与从容。
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年,他为田汉同志的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歌》《码头工人》《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卖报歌》等儿童歌曲。
聂耳的创作进入“井喷”时期,正是民族危机极为深重的年代,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对革命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毅然以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站在斗争的前列,在歌声中发出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1935年,聂耳又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等插曲,为电影《逃亡》创作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插曲《铁蹄下的歌女》。另外,他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在短短的两年中,他为我们创作了40余首充满战斗激情和富于劳动人民感情的歌曲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不朽的民族战歌最初的灵感源于聂耳参加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慰问活动。
1933年2月的一天,北平抗日救国会(由北平地下党领导)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长杜重远率领音乐家聂耳、著名电影导演张慧冲等40余人来到热河,一边慰劳辽西义勇军,一边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而这支辽西义勇军,正是电影《风云儿女》中“义勇军”的原型。此行,聂耳接触到了《义勇军誓词歌》,并被深深感动。
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田汉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抗日救亡的电影《风云儿女》,刚写完电影故事就被反动派逮捕,主题歌的歌词是在狱中完成后托人带出来的。聂耳听说《风云儿女》还差一首主题歌,主动去找编剧之一的夏衍,主动承担了作曲任务……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片头和片尾处,《义勇军进行曲》两次响起,激荡人心,引发全场观众齐声跟唱……随着《风云儿女》在全国的上映,《义勇军进行曲》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聂耳的老战友、中国音乐家协会原名誉主席吕骥在评价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时说:“聂耳的歌曲作为时代的战歌,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唱出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鼓舞起群众抗日救亡的斗争意志,使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的群众情绪沸腾起来,给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安协投降政策以沉重的打击。”
纪念
1935年春,上海的白色恐怖日愈加剧。2月,田汉、赵铭彝等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4月1日,又有国民党政府将逮捕聂耳的消息传来。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战士,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暂时躲避一段时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东渡日本。
7月17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在日本鹄沼海滨游泳时,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逝世时年仅23岁。
著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聂耳逝世后曾撰文评价:“聂耳先生之死是中国大众音乐的一个最大损失,几乎是等于音乐之国里失掉一个东北,东北可以收回,聂耳不能复活,这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啊!”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回顾、纪念这位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天才的人民音乐家——
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许多年轻人,是唱着聂耳、冼星海的歌曲走向革命的。他们两位是‘伟大的音乐家’。”
田汉是聂耳的亲密战友,又是聂耳走向革命的引路人。他说:“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由于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的人民中间,喊出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是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艺术创作无往不胜的道路。”
与聂耳齐名的音乐家冼星海评价他:“他是个划时代的作曲家,他是个民族呼声的代表者……聂耳先生能摆脱旧社会音乐的环境,而创造出新时代的歌声来,就是他给中华民族新兴音乐一个伟大的贡献,他创造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种民众音乐……他已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新兴音乐的大路。”
为民族的解放而呐喊、战斗的音乐家是不朽的!
玉溪作为聂耳故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讲述聂耳、纪念聂耳。2022年,玉溪市又举办了“聂耳和国歌”音乐文化系列活动,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更好地弘扬国歌精神。这应该是对聂耳最好的纪念了。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