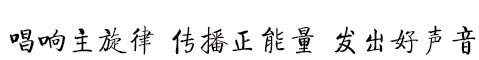□ 靳怡希
“对本质的任何探求,比不上从头顶轻轻飘落的一片树叶,比不上墙角偷偷开放的一朵野花。”无论是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掀起的云南旅游热潮,还是陶渊明、梭罗等人对原生自然生活的追求,都证明着人们对生活本质和劳碌一生之后境遇的期待也许是一个似桃源般的归处,先锋作家马原也不例外。经历过由五指山到阿里山、由阿里山到武夷山的路途后,他最终与他的“桃源”相遇在西双版纳的南糯山姑娘寨。2012年,马原来到云南西双版纳探望撒娇派诗人默默,在这里,他深深地被古茶树、孕育茶树的清泉和充满原始神秘色彩的爱尼人的历史所吸引,由此,这个“叫马原的汉人”便定居在了南糯山。马原亲切地称南糯山为他“最后的故乡”,他写《姑娘寨》的初衷就是“为自己的故乡树碑立传”。
爱尼是哈尼族的一个支系,任何族群都拥有自己的信仰,南糯山的爱尼人便有着根深蒂固的森林崇拜和祖先崇拜,这是他们向世界和生命诉说的方式。这个族群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这种口耳相传的历史的不确定性为定居于此的马原提供了可供想象和重塑的写作土壤。在《姑娘寨》中,马原用“一”“二”“三”章节名表示所包含内容为现实生活叙述,在这些情节里,“我”和好友默默、虚公谈茶谈酒谈生活,谈南糯山中寨的最后一任祭司别样吾和巫师的后代贝玛,而穿插于其中的“a”“b”“c”章节则叙述了“我”与爱尼人祖先帕亚马的相处故事。对于汉人来说,祖先似乎是很遥远的存在,虽然家里依然设有供桌,但每逢佳节才会“例行公事”般去烧纸钱祈求亲人保佑,从疏离程度和祖先的功能角度看,我们汉人的祖先好像与圣人、神仙已无不同了。所以汉人马原与六百三十七岁的爱尼人的祖先帕亚马可以像朋友般相处,正是爱尼人祖先观念的投射。除此之外,爱尼人坟山上的每一棵树都拥有一个家庭,“爱尼人没有给祖先挂牌位的传统,列祖列宗就被埋在本家的树下,之后沿着根须、树干和枝叶向上,在阳光雨露中聚会”。在纪录片《文学的日常》中,马原说,如若爸妈能和孩子埋葬在相邻的两棵树下,依托长在一起的树冠便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拉拉手”。这不由让我想到当年同样在云南的九叶诗人穆旦穿过胡康河谷时所作的《森林之魅》:“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吸引马原的不仅是爱尼人可以自由和祖先平等相处的这种区别于汉人的祖先观念,更是观念背后爱尼人与森林等自然万物共生和平等相处的生活模式:人以为的所谓其他生物,和我们其实处在同一个时空。
马原曾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信奉者,这与爱尼人的观念相契合。在《姑娘寨》中,末代祭司别样吾去寻找小巫师贝玛,马原习惯用“运气”来概括这种命中注定:“别样吾运气不错,他来的时候贝玛刚好在;所以他不必自己从两级高高的土台上下去;他在走的时候,也不必喊人帮忙,也就免去了喊不到人的窘况。所以说别样吾运气不错。”爱尼人则倾向于将这种命中注定归结为“是祖先的意思”。在巫师贝玛的孩子——一个将会成为爱尼人祭司的孩子出生时,贝玛的奶奶——活到九十九岁已经能够被称为祖先的“人瑞”在那一天走了,“冥冥中的一切都有它自身的秩序”,这既是祖先的安排,也是上天的安排。马原与他们都是忠实的宿命论者,我也是——马原与姑娘寨的羁绊是命中注定,我成为马原《姑娘寨》的读者同样是命中注定。
在《姑娘寨》中,马原延续了先锋写作的笔法和他所擅长的“叙述圈套”技法,勾勒出了带有民族性和传奇性的爱尼人史诗情节。《姑娘寨》的前身是2018年6月马原前后发表在《十月》杂志和《中篇小说选刊》上的两部中篇小说《姑娘寨的帕亚马》与《谷神屋的贝玛》,集结于《姑娘寨》时呈现出章节间错落并行的特点,读者初读《姑娘寨》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不过按照马原的话来说,生活本身并不是一个逻辑过程,小说当然也没必要呈现出规矩的连续性。马原的这种叙事手法与含有祭司、巫师、原始森林等元素的爱尼人自身带有的民族传奇性和秘境神秘色彩相辅相成,于是他顺利地把所构建的爱尼人神性世界的真实性传递给了读者。我想,没有人会怀疑南糯山的某棵古树曾是一个“腰间系一根皮绳,身前身后牢牢拴着两片肥硕柔软的巨大的叶子”且随身携带着火种的爱尼人祖先的家。
姑娘寨是马原命中注定的终老之地,他在这片土地上晴耕雨读,与爱尼人及他们的普洱茶树朝夕相伴。他翻阅《西双版纳哈尼族简史》,他理解帕亚马保护祖宗树的执着和刚拉为“渡族人”过澜沧江而交出金勺子的大义,他的《姑娘寨》为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耕”续了一片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