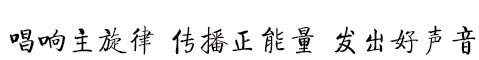□ 付冯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在战火中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凭空而生,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文化基因和“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民族危亡关头,人民音乐家聂耳以其充满抗争力量的音符,成为了伟大抗战精神的嘹亮先驱。他创作的抗战救亡音乐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以震撼心灵的旋律激励着全民族反抗侵略的共同意志,其所承载的反抗精神与家国情怀,不仅深刻影响了救亡运动进程,更成为抗战精神的不朽象征。
抗日战争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抗日战争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血与火的战争史,更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熔铸史。中国人民在14年的浴血奋战中,凝聚起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抗战精神的内涵:“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伟大抗战精神不仅是中国人民在面对外来侵略时展现出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爱国主义。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就以深厚的家国情怀著称于世,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源远流长,早已融入文化血脉之中,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奉献,到近代无数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这种对家庭的守护、对国家的忠诚,始终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底色,也是我们民族历经磨难却总能凝聚力量、生生不息的重要密码。这种情怀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的激发,是抗战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观,在抗日战争中以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唐淮源等为代表的抗日将士与侵略者殊死较量以身殉国,凸显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中华儿女血脉中涌动着无所畏惧、刚健有为的民族血性基因,有着不畏强暴、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面对侵略者的血腥暴行,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军民焕发出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篇章。面对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一大批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终于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始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砥砺奋进、勇往直前。
聂耳是抗战音乐的领军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抗日救亡歌曲也伴随着救亡运动的蓬勃兴起而产生,成为唤起民众、教育民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其中,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抗战歌曲之一。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工作者“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虽然聂耳英年早逝,未能经历全面抗战的烽火岁月,但他“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他的音乐创作始终与民族危亡紧密相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聂耳用音乐作为战斗号角和革命武器,为全民族解放呐喊,其作品所承载的“起来反抗”的勇气、“团结御侮”的信念,成为全民族在苦难中挺立的精神支柱;所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家国情怀,成为抗战精神的重要符号象征,深刻影响了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
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救亡运动席卷全国。身处时代洪流中,目睹山河破碎、民众苦难,聂耳以音乐为武器,将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反抗侵略的勇气融入音乐创作。他认为“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这种“为大众呐喊”的使命感,让他的作品始终扎根于民族救亡的土壤。聂耳和田汉合作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插曲《毕业歌》,在社会的苦难、国家危难的时刻,用“战还是降”“做奴隶”还是“做主人”的尖锐诘问与选择,让青年直面救国责任,呼唤青年“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鼓励作为“社会的栋梁”的青年“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歌曲以激昂的旋律、“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的主动姿态,奠定了中国抗战文艺“不屈叙事”的基调。无数青年高唱着《毕业歌》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这首歌曲不仅成为青年战歌,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代表着青年们的爱国情怀和抗日决心。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的《铁蹄下的歌女》,通过来自沦陷区底层女性的血泪控诉,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民族救亡的集体呐喊,打破了“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刻板印象,体现了歌女的爱国情感和抗争意识。聂耳、田汉为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的主题曲《前进歌》,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怒吼——“我们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让我们结成一条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向着自由的路前进!”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呐喊,将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意志浓缩为震撼人心的旋律,吹响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战斗号角。《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则聚焦底层民众的苦难与力量,唱出“团结起来、冲破枷锁”的呐喊。聂耳作曲的抗日救亡歌曲,跳出了单纯的悲叹,始终传递抗争的力量,与抗战精神高度契合,大多以激昂奋发的旋律、短促有力的节奏、通俗易唱的形式,表达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聂耳是抗战音乐的领军人物之一。
《义勇军进行曲》是抗战精神的不朽象征
《义勇军进行曲》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具标志性、获得最广泛认同的作品,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写照,在激励国民的爱国热情、唤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宣传鼓动民族自救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它所唤醒的不只是一个民族的抗争意志,更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精神标识——伟大抗战精神的象征。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问世后迅速风靡全国,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从城市到乡村,《义勇军进行曲》被广泛传唱。艺术家丰子恺形容《义勇军进行曲》的传播情况时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军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强烈呐喊,唤起了民众反抗侵略的决心,激发了全民抗战的热情。它不仅是战斗号角,也重塑了社会心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抗争主题强化了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象征。歌中始终传递反抗与必胜信念,与抗战精神高度契合,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精神支柱。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中,聂耳自觉地摒弃了“精英化”表达,采用通俗、激昂的旋律(如《义勇军进行曲》的号角式开头),让工农兵、学生、知识分子都能听懂、能传唱。这种接地气的创作,让“抗争”从口号变为全民行动,为抗战时期全民族抗战的动员奠定了精神基础。1935年聂耳不幸遇难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但他的作品在抗战中成为精神武器——前线战士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冲锋,后方民众以其旋律组织募捐、宣传抗日,海外华侨也通过他的音乐凝聚支援祖国的力量。
在国际上,《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拍摄的抗日战争纪录片《四万万人民》(“The 400 Million”)中,有一组中国群众在升旗仪式中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镜头。1943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抗战歌曲集》(“Songs of Fighting China”)中,《起来》(“Chee Lai”,即《义勇军进行曲》)被认为是当时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歌曲,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抗战歌曲。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是第一位公开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外国艺术家,他和刘良模合作,录制了名为《起来:新中国之歌》(“Chee Lai :Songs of New China”)的唱片,收入了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一组中国抗战歌曲。他多次在援华集会上用中文和英文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将演出收入捐赠中国抗战前线。二战结束前,《义勇军进行曲》还被反法西斯盟军采纳为庆祝胜利的演奏曲目。
《义勇军进行曲》倾注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郭沫若在为聂耳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唱出了特定时代人民的呼声,更唱出了刚强不屈、勇往直前的国之魂魄,凝缩着国家和民族的苦难辉煌,传承着国家和民族的不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聂耳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永远激荡中国人的不朽旋律,鼓舞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玉溪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