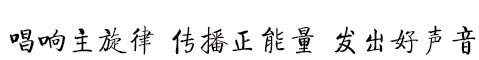□ 坝汝明
少年时的夏天,仿佛总被蝉鸣拉得很长,而躲猫猫,就是嵌在这段时光里最鲜活的注脚。
我们总爱选日头偏西的时候开场,影子被拉得老长,正好给躲藏添了几分便利。找的人蒙眼数数,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一、二、三……”躲的人早猫着腰四散开来,心跳得比脚步还快。有人往柴房的缝隙里钻,有人贴着墙根屏住呼吸,而我偏爱房屋旁的那个稻草垛,蓬松又温暖,钻进去,世界就只剩头顶一小片天和稻草的清香。
记得那回,我躲进草垛没多久,午后的困意便涌了上来,稻草的触感像极了家里的旧棉絮。不知睡了多久,夜里的凉气把我冻醒。睁开眼,天已经黑透了,只有远处窗户里漏出一点昏黄的光,还有大人们此起彼伏的呼喊声。我扒开草垛钻出来,带着一身草屑,看见母亲跑过来时眼里的光,又后怕又忍不住想笑。原来我把一场游戏,睡成了大人的一场虚惊。
也有过吓得不敢再玩的日子。村东头有间废弃的瓦房,墙上的灰泥都掉光了,院里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那天我们几个商量着,要躲进瓦房最里面的隔间,定能让找的人急得跳脚。可刚推开门,草堆里“嗖”地窜出一条大蛇,粗得像小孩的胳膊,带着腥味的信子吐了吐,我们想喊都没喊出声,转身就往外跑,鞋子跑掉了都不敢捡。后来再路过那间瓦房,总觉得墙缝里都藏着一双冰冷的眼睛,躲猫猫的邀约,也歇了半个月。
还有一次,我躲进了灶房后的灰洞,那是用来存放草木灰的地方,黑乎乎的,最是隐蔽。等游戏结束,我才发现自己从头到脚都沾了一层灰,连鼻孔里都有。回家的路上,风一吹,身上就掉“粉”,怕被母亲骂,我在村子前面的池塘边用树枝拍打了一刻钟,用冷水反复搓洗,可耳后、指甲缝里的灰,怎么也洗不干净,最后还是顶着一张“小花脸”回了家,挨了顿轻揍,却也觉得值——毕竟,我赢了那场游戏。
如今想来,那时的快乐多简单啊,不需要手机,不需要玩具,一群人,一个院子,欢乐就能把整个夏天都填满了。现在的孩子有了更精致的游戏机,大概不会懂,我们为什么会为一个草垛、一个灰洞而雀跃,为什么会因为一条蛇就留下那么深刻的记忆。
岁月跑得比当年找我们的小伙伴还快,少年时的稻草垛早没了,瓦房也拆了,连一起躲猫猫的人,都分散在了天南海北。可每当想起那些夏天,想起草垛里的阳光,灰洞里的笑声,还有母亲那声带着焦急的呼喊,心里还是会暖暖的。
原来有些快乐,真的会像草垛里的余温,藏在记忆深处,不管过多少年,一想起,就感觉自己还是那个没长大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