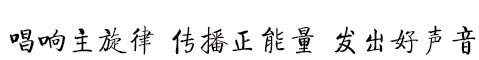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聂耳短暂的艺术生涯犹如一颗璀璨的流星,照亮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他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在民间音乐的沃土中深植根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汲取养分,又在西方音乐理论的海洋里拓展视野,最终在《义勇军进行曲》等音乐作品中完成了创造性转化。这首战歌既蕴含中国五声音阶的韵味,又具备西方进行曲的雄壮结构;既富有国际革命歌曲的战斗精神,又融入了劳苦大众的呼吸节奏,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呼声的完美结晶。聂耳的音乐创作经历构成了一幅多元文化交融的立体画卷,他的艺术实践昭示我们:真正的文化创新,源于对本土传统的深刻理解,并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优秀文化,在兼容并蓄的文明交流互鉴中,方能奏响时代的强音。
民间音乐启蒙,传统文化浸润
聂耳出身于中医世家,他音乐启蒙最早源于家庭环境的濡染。他的母亲彭寂宽爱好民间音乐,聂耳在襁褓中时,她常以玉溪花灯等民间曲调哄他入睡。聂耳后来回忆说,儿时母亲吟唱的民谣是他“有限音乐修养”的重要源头。聂耳虽未接受系统的经学教育,但在家庭的影响下,他自幼便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两个哥哥聂子明、聂叙伦回忆说,因为聂耳年纪最小,母亲格外疼爱他,但并没有让聂耳沾上娇生惯养的习气。她从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每天要他们按时读书写字,并给他们定了不准说谎话、不要随便接受别人赠送的钱物等要严格遵守的家规。每晚临睡前,她喜欢坐在床上说书给孩子们听,说的都是《柳萌记》《孟姜女》之类民间流传的故事,那些书尽是七言或十言写成的,可说可唱。聂耳非常爱听,在母亲说书时总是聚精会神。她不论家里怎样困难,也要想方设法供孩子们进学校读书。聂耳的传统文化感知源于家庭家教家风的滋养,他在1930年10月19日写的日记中回忆:“民国六年春,六岁时,入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校初级一年级。在先我没有入过幼稚园也没有入过私塾,但那时我已认识了一两千单字。”从没有上过幼稚园或者私塾,却能认识一两千单字,这些文字认知的基础,正是家庭启蒙的结果。聂耳四岁时,他的父亲聂鸿仪就病逝了。聂耳在日记中写道:“爸爸的死,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指示着我应走的道路。走进他的房里,他心爱的那些烟具依旧平静地躺在床上,他教我认的图画方字杂乱地摆在烟盘子里,仿佛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从家庭与传统文化中,聂耳继承了深厚的文化血脉。
丰沃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也滋养着少年时的聂耳。1922年春,10岁的聂耳向邻居木匠学习笛子、二胡等中式乐器,这标志着聂耳音乐生涯的开始。1922年春至1925年春,在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求学期间,聂耳广泛接触洞经会、滇戏班等。曾与两个兄长一起进入昆明的洞经乐社“宏文学社”,学习洞经音乐和乐器演奏。聂耳在日记中回忆说:“民国十三年冬,十三岁时,高小毕业。”“在高小的后两年,成绩都是全班第一,曾任学生自治会的会长。”“我演新剧、双簧就是在这年开始。音乐已成全校之冠。”1925年春至1927年夏,在云南第一联合中学求学期间,聂耳加入了该校“课余音乐社”,担任笛子、二胡演奏员。在此期间,聂耳常流连昆明的茶馆、戏台等场所,观看滇剧等民间戏曲。1927年秋至1930年夏,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聂耳加入学校国乐研究社,据校史档案(《省立一师社团活动档案》1928年10月)记载,他曾在昆华图书馆举办的雅集中演奏《平沙落雁》,并讲解“雁阵排列如乐曲结构,疏密有致方显韵味”。受母亲的影响,聂耳毕生对民间音乐怀有浓厚的兴趣。在1933年5月28日写给母亲的信中,聂耳说:“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
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热爱和学习,使聂耳掌握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音调及其调式构成,这为他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4年,聂耳在百代唱片公司任职期间参与筹建“百代国乐队”,改编创作了《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昭君和番》等民族器乐合奏曲。其中,《翠湖春晓》是以洞经音乐曲牌《老卦腔》(亦称《宏仁卦》)为素材改编的,《金蛇狂舞》是根据民间乐曲《倒八板》改编。他还根据花灯曲牌《玉娥郎》改编创作了歌曲《一个女明星》。这些作品既保留了民间音乐的韵味,又注入了现代音乐的表现力。
民间音乐为聂耳提供了最鲜活的音乐语言和最真实的人民情感。他不仅学习和改编民间音乐,更从中汲取旋律、节奏、音调的养分,并创造性地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五声性调式是以宫、商、角、徵、羽五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音乐调式体系。在聂耳创作的歌曲中,有半数采用了五声性调式。他运用各种五声性调式写作了《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卖报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新女性》等反映劳苦大众生活、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歌曲。曾与聂耳共同战斗的音乐家吕骥评论说:“他(聂耳)既不像一般人囫囵吞枣将两洋歌曲贩到东方来,也不是以乡间民歌一类的小曲,来换头改面。”吕骥所说的“两洋歌曲”,应是指西洋歌曲和东洋歌曲,即西方音乐及日本音乐。聂耳曾收集和研究了许多民歌调子,他从来不在形式上去模仿,而是把民族化、大众化的生活场景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后融入音乐作品中,通过音乐艺术语言的形式再现社会劳作场景及身边熟悉的小人物(范晓晶:《聂耳音乐作品中民族元素研究》)。
聂叙伦回忆说:“他(聂耳)从小爱听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对‘精忠报国’‘舍生取义’等观念有很深印象。”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忠义精神、民族气节、家国情怀,以及“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聂耳的创作动机与艺术追求。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中华传统文化为聂耳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根基与价值支撑,使他的音乐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表达,成为唤起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情的武器。
西方音乐理论技术赋能,革命文艺理论明确创作方向
扎根民间的音乐实践,塑造了聂耳对大众声音的敏锐感知,奠定了他的创作根基;而当他将目光投向西方音乐世界时,技术与精神的双重滋养,为其创作注入了更广阔的艺术可能。
少年聂耳对音乐的学习,不仅涵盖了花灯、洞经等民间音乐和二胡、三弦、月琴等民族器乐,也涉及小提琴、钢琴等西方器乐。1927年秋,15岁的聂耳向邻居、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音乐教师张庾侯学习小提琴。张庾侯对聂耳的音乐天赋十分赏识,不仅教会他小提琴演奏的基础,更激发了聂耳对这一乐器的热爱。他与聂耳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超越了单纯的技艺传授,这段特殊的师生情谊对聂耳音乐道路产生了长远影响。这是目前可知聂耳音乐生涯中首次接触西方弦乐器。小提琴是西方古典音乐的重要乐器,其丰富表现力和音色,吸引了年轻的聂耳,他意识到要走向更广阔的音乐世界,掌握小提琴是重要一步。1931年初,在上海云丰申庄打工的聂耳,因帮张庾侯代租电影拷贝,收到其寄来的100元酬金。他把一半汇给母亲,剩余的买了一把德国制造的二手小提琴、几本乐谱和一件冬衣。终于拥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聂耳十分兴奋,他在日记中写道:“Violin自然是能使人心境舒畅”“愿与此琴终身为伴”。此后,这把小提琴始终陪伴在聂耳身旁。
在昆明时,聂耳曾向法籍音乐教师伯希文请教音乐基础理论及弹奏钢琴的知识。在上海,进入联华歌舞班后,聂耳开始系统地学习音乐知识,他钻研琴谱,向明月歌剧社的提琴“小老师”王人艺请教小提琴,跟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首席中提琴师、原籍奥地利的普杜什卡学习小提琴,跟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俄籍教授阿克萨柯夫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他还到北平向清华大学的俄籍音乐教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通过学习,聂耳了解西方音乐的旋律结构、和声体系、乐器性能与表现技法,对大、小调的旋律、音调及和声等作曲技法有所了解,这些学习经历同样为他的音乐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学习西方音乐理论技巧提升艺术能力的同时,革命文艺理论促使他形成了批判性的音乐观念和明确的创作方向。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他参加学校组织的“读书会”,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读物,他学会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矛盾。在学习、生活、创作和革命活动中,他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斗争意志。他在1930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看了几篇革命文学论文,指示给我现在艺术运动的主要任务是要大众化。”“今后我的研究和创作文艺方针将改变了,不再作个人的呻吟或以个人的革命性的表现去影响群众。”他宣告将“向着新的艺术运动的路上跑去”。
聂耳少年求学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新思想广泛传播时期。他自幼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中华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人精神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价值观,加上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思潮,培养了聂耳强烈的民族意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罪行,聂耳反复思考怎样创作革命音乐,更好地服务于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1933年初,经田汉、赵铭彝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田汉的影响下,他的世界观、音乐观发生转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知道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他创作的题材更多地转向写实方面,内容上也更积极向上,创作天赋得到显现,创作技法得到提高,作品主题和风格逐渐成熟,他的音乐将民族音乐语言与时代精神高度结合,成为中国音乐界“新音乐”的开端。
聂耳的好友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路》中评论说,聂耳没有机会受正规的音乐教育,他的作曲存在一些技术上的缺点,“可是在善于继承祖国民间音乐传统、接受欧洲音乐的健康豪迈的作风和准确有力地处理中国语言方面,聂耳却有别人难于企及的长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也有类似的看法,在《聂耳的道路》中他评论说,聂耳一方面十分尊重自己民族的音乐传统,另一方面也努力钻研并借鉴世界革命音乐和古典音乐的成就。他的创作不为民族固有的音调体系所局限,他从音阶、节奏和节拍等方面吸收西欧的先进因素。
进行曲是一种富有节奏步伐的音乐体裁,是西方音乐的重要体裁之一。在写作《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等反侵略战歌时,聂耳更多运用进行曲的体裁形式,采用进行曲常用的步伐式明快节奏,同时在五声音调的基础上,借鉴外国革命歌曲的音调,融入大调式的旋法,使旋律、音调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同时,具有时代性、大众化的特点和雄壮、昂扬、勇往直前的音乐形象,增强了歌曲号召性。聂耳对中西音乐特点的深刻认知和运用,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得到完美呈现。他没有拘泥于中国传统音乐的惯用创作手法,也没有照搬西方歌曲常见的创作模式,而是根据歌词内容,大胆地创新和突破。他以西方2/4拍进行曲为框架,融入中国五声音阶与劳动号子节奏。开头以弱起的“2-5”四度音程为动机,是对《国际歌》的借鉴,像是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逯也萍:《聂耳与〈义勇军进行曲〉》)。前奏的三连音借鉴《马赛曲》的号角式音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休止符处理,则通过节奏顿挫强化民族危机感,使西方曲式承载中国情感。中国歌曲的民族特色与西方的进行曲风格有机融合,使《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一首西洋体裁的中国作品,易于被大众所接受、掌握和学习。这种“中西合璧”的创作,使聂耳的音乐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也成为文化交融的典范之作。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西音乐水乳交融的双重滋养,成就和奠定了聂耳作为人民音乐家的崇高地位。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融,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聂耳把民族音调、大众语言与时代主题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性、时代性与人民性的音乐风格,奠定了中国新音乐的方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重温聂耳音乐轨迹中的文化交融智慧,我们看见的不仅是一位音乐家的成长史,更是一个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案例,在坚守文化根脉中开拓进取,在文明互鉴中铸就文化自信,才能奏响“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乐章。
(作者单位:中共玉溪市委党校) |